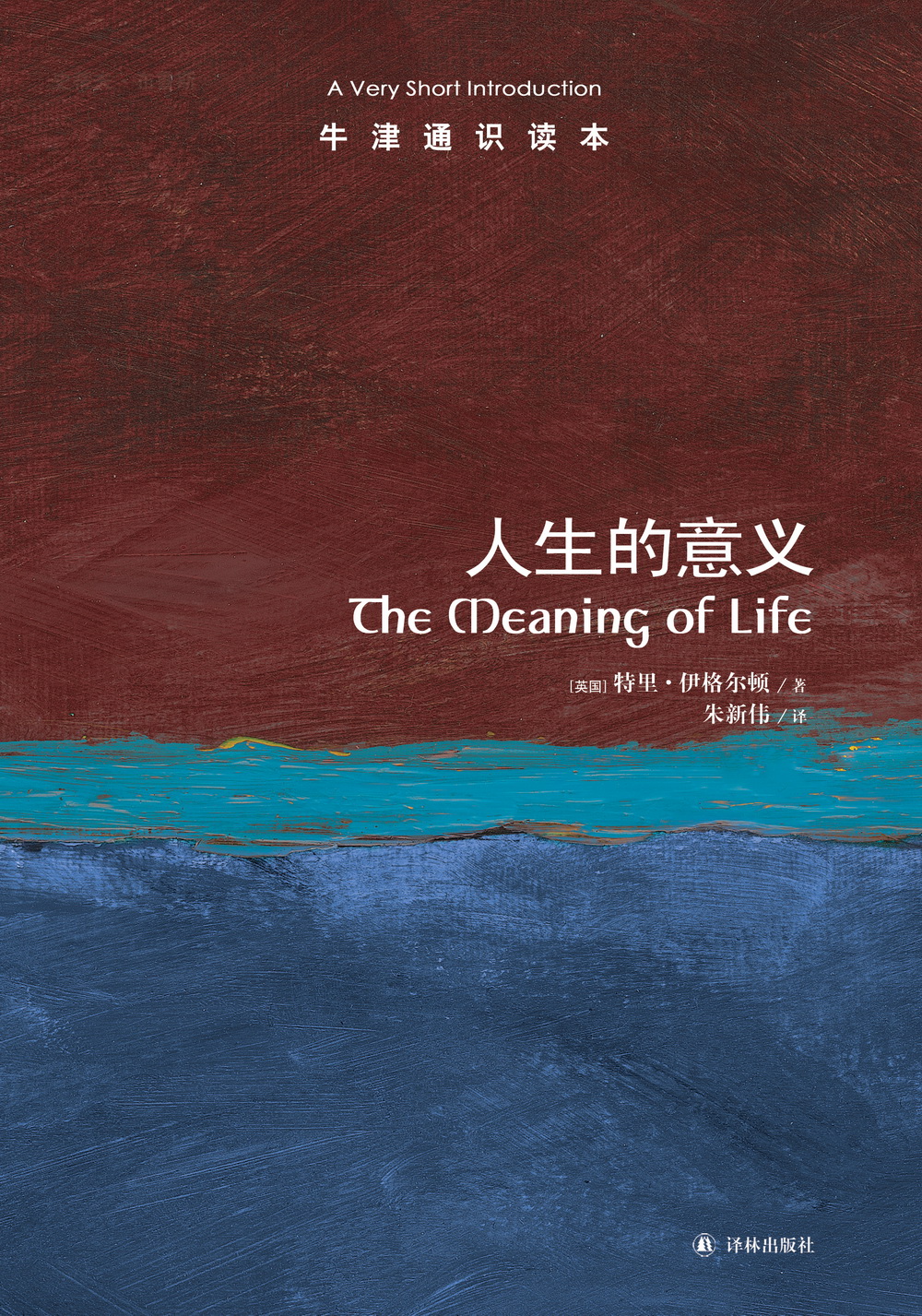
【名人评价及推荐】
使我感到惊叹的倒不是这一沉重的话题能够写得如此通俗活泼,而是一本如此飘逸生动的小书居然能够切入到如此深邃的哲理之中,这是我从未见过的。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邓晓芒
让人赞叹不已。这是给众人看的哲学,最符合“哲学”这个词的本义。……(伊格尔顿)说理透辟,笔触轻盈。我深为折服。
——《卫报》 西蒙•詹金斯
【编辑推荐】
《人生的意义》是英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一部力作,从哲学角度极深地切入人生意义问题,为这个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提供启示。国内著名哲学学者邓晓芒作序力荐。
我们都曾对人生的意义感到困惑。这个问题是否有答案?答案是否取决于我们?或者它不过是一个伪问题?在这部充满睿智和生气又能激发思考的作品中,特里·伊格尔顿展现了许多世纪以来的思想者,从莎士比亚、叔本华到马克思、萨特、贝克特,对人生意义问题的探索。作者知道,“本书的许多读者很可能会像怀疑圣诞老人的存在一样怀疑人生意义”,但同时又认为,在需要寻求共同意义的当今之世,我们有必要回答这个所有问题背后的问题。
特里·伊格尔顿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约翰·爱德华·泰勒”英语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近年出版的著作包括:《神圣的恐怖》(2005)、《英国小说导论》(2004)、《理论之后》(2003)、《温柔的暴力:悲剧的观念》(2002)、《文化的观念》(2000)、《后现代主义的幻象》(1996)、《文学理论导论》(1996年第2版、1983年第1版)等。
引言
任何一位鲁莽决定用这个标题来写书的作者最好都准备收到一个邮包,邮包里装满笔迹潦草、附寄各种复杂的符号图表的来信。人生的意义,这样一个主题既适合疯子来写,也适合喜剧演员,我希望自己宁可是后者而非前者。我尽量用轻松明快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高尚的主题,同时又不失严肃性。但是,这整个主题涵盖太广,近于杂乱,而学术界的讨论范围要小很多。
多年前,我还在剑桥大学念书,视线被一篇博士论文的题目吸引,该论文题为“跳蚤的阴道系统略论”。有人会猜想,这个论文题目不太适合近视眼患者作研究;但这个标题提醒着一种动人的谦恭,这种谦恭我很明显没有学到。我至少可以保证的是,这是少数几本以“人生的意义”为书名,却没有讲述罗素和出租车司机那个段子的著作之一。感谢约瑟夫·邓恩,他阅读了本书手稿,并给予了宝贵的批评和建议。
第一章 提问与回答
哲学家有一个惹人讨厌的习惯:喜欢分析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我也准备以分析问题的方式开始我的论述。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真问题还是只是看上去像个问题?是否有什么能充当答案?或者它只是一个伪问题,类似于传说中的牛津大学入学考试题目,只有一句话:“这是一个好问题吗?”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初看好像和以下问题差不多:“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在哪?”“象牙是什么颜色的?”但真的差不多吗?是不是更接近这个问题:“几何学趣味何在?”
有些思想家认为人生的意义问题本身并无意义,之所以如此认为,有一个相当坚实的理由。意义是一个语言层面的东西,无关实体。它是我们讨论事情的某种方式,而非像纹理、重量、颜色那样,是事物本身的属性。一颗卷心菜或一张心电图,其本身没有意义,只有当我们谈论它们的时候它们才有意义。照此推论,我们可以通过谈论人生来让人生变得有意义。但即便如此,人生本身还是没有意义,就像一朵浮云本身没有意义一样。比如,声称一朵浮云为真或为假,这根本行不通。真与假仅是我们关于浮云所作的人为命题的功能。与多数哲学主张一样,这个主张也存在问题。后面我们会考察其中的一些。
我们一起来简单地看一个比“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更唬人的质问。也许我们所能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切事物会存在,而不是不存在?”为什么会存在那些事物,我们首先可以问其“意义何在”?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是真是伪存在争论,不过大多数神学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对多数神学家来说,答案就是“上帝”。上帝之所以被称为世界的“造物主”,不是因为他是一切创造者的创造者,而是说,上帝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因。据神学家说,上帝乃存在之基础。即使这个世界从不曾开始,这一点对他来说也依然成立。即使某些东西亘古就有,他依然是一切事物之所以存在的终极因。
“为什么存在万事万物,而非一片虚无?”这个问题可以粗略地转换成“这个世界是如何产生的?”它可被视为因果论的问题:在此情形下,“如何产生”即指“从哪里产生?”但这显然不是这个问题真正想问的。如果我们努力通过讨论世界万物从哪里产生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找到的那些原因就包含在这个世界当中;这就变成循环论证了。只有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原因——一个超验的原因,正如设想中的上帝——才能避免以这种方式被拖回论证本身。所以,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关乎世界如何产生,并且至少对于神学家来说,也不关乎世界的目的,因为在神学家眼中,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任何目标。上帝并不是宇宙工程师,在创世时有一个从战略上经过盘算的目的。上帝是一个艺术家,创造世界只是为了自娱自乐,为了享受创世这个过程本身的乐趣。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觉得上帝有某种扭曲的幽默感了吧。
“为什么存在万事万物,而非一片虚无?”毋宁是一种惊叹:我们很容易推想原本是一片虚无,事实上却最初就存在着一个世界。也许这就是维特根斯坦说“玄妙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样貌如何,而是这个世界以这样的样貌存在着这一事实”的时候他心里部分所想的。有人可能会说,这是维特根斯坦版的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德语叫做Seinsfrage。海德格尔想追溯到“存在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他关心的不是特定实体如何产生,而是另一个让人迷惑的事实,即究竟为什么会有实体存在。这些实体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它们本来很可能并不会出现。
不过,许多哲学家,不单单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下的哲学家,认为“存在是怎么产生的”是一个典型的伪问题。在他们看来,即使有解答的可能,也不只是难以回答;令人深深怀疑的是,也许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回答。在他们看来,提这种问题就像一个笨头笨脑的条顿人大吼一声“哇!”。“存在是怎么来的”对一个诗人或神秘主义者来说也许是一个有效的问题,对一个哲学家却不是。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诗学与哲学两个阵营之间壁垒森严。
在《哲学研究》这本著作中,维特根斯坦对真问题和伪问题的区分非常敏感。一段话可能在语法形式上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却不是。或者,语法可能会误导我们,让我们把两种不同的命题混淆起来。“同胞们,一旦敌人被打败,在胜利的时刻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听起来是一个期待答案的疑问句,但实际上是一个反问句,回答“没有什么!”是不明智的。这句话诘问的语气仅仅是为了提升气势。“那又怎么样?”“你怎么不滚?”“你看什么看?”听起来是问话,实则不然。“灵魂在身体何处?”可能听起来像一个合理的问题,但仅仅是因为我们把它当做“肾脏在身体何处?”一类的问题来思考。“我的嫉妒心在哪儿?”这个问题具有真问题的形式,但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意识地把它和“我的腋窝在哪儿?”当做一类问题。
维特根斯坦进而认为,大量的哲学难题都源于此类语言误用。比如,“我有点痛”和“我有顶帽子”在语法上是相似的,这种相似性可能会误导我们去认为,能够像拥有帽子那样拥有疼痛,或者是拥有更一般的“感受”。但是,说“来,拿着我的疼痛”这种话是奇怪的。询问“这是你的帽子还是我的?”是有意义的,但要问“这是你的疼痛还是我的?”听起来就怪怪的。想象一下几个人在房间里,像玩击鼓传花一样传递疼痛;随着每个人轮流痛得弯下腰,我们大叫:“啊,现在他正在拥有疼痛!”
这听起来愚蠢,实际上却有一些相当重要的暗示。维特根斯坦将“我有点痛”和“我有顶帽子”在语法上进行区分,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我”与“他”这样的人称代词的用法,而且颠覆了将个人感受当做私有财产的传统思维。实际上,我的感受比帽子更具私人性,因为我可以扔掉自己的帽子,但不能扔掉疼痛。维特根斯坦告诉了我们,语法如何蒙蔽着我们的思维;他的论断具有激进的,甚至是政治上激进的后果。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解决这些疑问,而是消解它们——去揭示它们所产生的根源,即各种他所谓的“语言游戏”之间的相互混淆。我们被自己的语言结构所魅惑,哲学家的工作是祛魅,拆解开词语的各种用法。由于语言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规整性,它很容易让不同类型的话语显得极为同一。所以,维特根斯坦戏谑般地引用了《李尔王》中的一句话作为《哲学研究》的卷首题词:“我来教你什么是差别。”
不单单是维特根斯坦这么想。尼采是19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在怀疑是不是出于语法的原因我们才无法摆脱上帝时,他已经比维特根斯坦先行一步。既然语法允许我们建构一系列名词,而名词代表独特的实体,那么,似乎也可以建构一个位于一切名词之上的名词,一个被称做“上帝”的元实体,若没有它,我们身边所有的小实体都将崩溃。然而,尼采既不相信元实体,也不相信那些日常的实体。他认为,诸如上帝、醋栗等独特客体的理念本身正是语言的具体化效应。就个体自我来说,他当然相信是这样的,“个体自我”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种省事的虚构。他在上面的评论中暗示说,也许存在着一种人类语法,在这种语法中,不可能发生具体化效应。也许这将是未来的语言,说这种语言的是“超人”(德文叫做Ubermensch),而超人已经完全超越了名词和单个的实体,自然也就超越了上帝之类的形而上学幻象。深受尼采影响的另一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这一论题上更为悲观。他和维特根斯坦一样,认为这种形而上学幻象深植于我们的语言结构之中,根本不可能消除。
序言
邓晓芒
英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 )前几年写了一本哲学书:《人生的意义》。他在书中坦承,他不是哲学家,他是以“喜剧演员”的轻松明快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崇高的主题的。的确,我们在这本薄薄的小书(总共一百来页)中到处遇到的是英国式的幽默和无伤大雅的调侃,但话题却是严肃而深沉的。使我感到惊叹的倒不是这一沉重的话题能够写得如此通俗活泼,而是一本如此飘逸生动的小书居然能够切入到如此深邃的哲理之中,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可以看出,作者虽然身为英国作家,而且研究的是最具感性色彩的文学理论,但明显深受大陆哲学如存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哲学和解释学的熏陶,并对这些非盎格鲁-撒克逊的思辨套路驾轻就熟。不过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大陆的两栖哲学家(既是分析的又是思辨的)维特根斯坦,后者的清晰明白是英美语言分析哲学最强有力的理论支柱。与分析哲学家不同的是,他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研究》上,这恰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罗素等人的分析的传统,也是他敢于并有兴趣认真对待“人生的意义”这样一个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毫无意义的话题的基础。俗话说,“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他比罗素更敏锐地听出了维特根斯坦话语后面的东西,而将分析哲学这一文学的天敌俘获为文学与思辨哲学结缘的纽带。
我们只要看看他对“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语义学分析就会发现,虽然他广泛运用了对词和意义的分析技术,但他的处理方式和分析哲学家们完全不同。他不是用分析来消灭这个问题(例如说,断言这个问题“无意义”),而是用分析来从语义层面的问题引向更深的存在层面的问题,亦即人生的悲剧处境的问题。“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悲剧最彻底、最坚定地直面人生的意义问题,大胆思考那些最恐怖的答案。最好的悲剧是对人类存在之本质的英勇反思,其源流可追溯至古希腊文化……最有力的悲剧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句,刻意撕掉所有观念形态上的安慰。如果悲剧千方百计告诉我们,人类不能照老样子生活下去,它是在激励我们去搜寻解决人类生存之苦的真正方案……”(第11页)。对悲剧的这种解释很新颖。悲剧并不像黑格尔的经典定义所说的那样,意味着两种同样合理的伦理力量的冲突通过主人公的牺牲而得到调解;相反,悲剧是对人的存在的一个提问,这个提问的答案是开放的。“人生没有既定的意义,这就为每个个体提供了自主创造意义的可能。如果我们的人生有意义,这个意义也是我们努力倾注进去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第29页)不言而喻,人生的意义更不是由别人规定好让你去实现的。我们现在通常的做法是,由政府颁布一种人生的意义,写在教科书里面从小灌输给孩子,以为只有这样孩子长大了才不会失去人生的意义,不会感到“空虚”。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做法。曾经有不少受过这种教育的青年满怀困惑地来问我,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一般回答说,人生的意义需要你自己去寻求,别人给的都不是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大学生,一涉及到人生意义的问题就很自信地背出从小学到的一套教条来,流露出不少得意,我却为此感到悲哀。我分明看到的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中国人个性的萎缩。
不过,本书的作者也不完全赞同这种把人生意义当做个人事业的观点,他认为这只是“传统智慧的观点”。(第31页)在这方面,他倾向于用(更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来补充个人主义的意义追求,这种宏大叙事并不是单独的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特殊性来设定的,但却是最终用来衡量人生意义的标准。他把这种标准称之为“意味深长的模式”,并认为,“倘若人类生活中没有意味深长的模式,即使没有单独的个人想这样,结果也会造成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全盘停摆。”(第43页)。当然他也不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归结为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客观规律”,但毕竟不能说,人类几千年以来一直都在乱碰乱撞,总会有某些确定一贯的东西是那些自由主义者和个性至上论者所公认的,或者虽然并不明确意识到,至少也是实际上用作自己判断的前提的。这种情况,作者更愿意用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来解释(第44-45页)。只不过这种不是人所有意设定的合目的性往往被人们归于不可见的上帝的安排。对于这种安排,人们要么听天由命,这就不用自己思考任何意义了;要么努力探索,这将导致无穷的痛苦。的确会有人为了摆脱这种痛苦而认为,即使有人生的意义,人还是不要知道这种意义为好。(第49页)这种犬儒主义的当代标本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作者在本书中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是我所见过的最到位的。“后现代主义坚称,只要我们还有深度、本质和根基,我们就仍然活在对上帝的敬畏之中。我们还没有真正把上帝杀死并埋葬。我们只是给他新换了一套大写的名字,如自然、人类、理性、历史、权力、欲望,诸如此类。……‘深刻的’意义总会诱惑我们去追寻那诸意义背后的元意义这种妄想,所以我们必须与之切割,才能获得自由。当然,这里的自由不是自我的自由,因为我们已经把‘自我’这个形而上学本质同时消解掉了。到底这一工程解放了谁,这还是一个谜。”(第16-17页)最后一句话是点睛之笔,也是神来之笔。
从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作家是萨缪尔•贝克特。作者在对贝克特的代表作《等待戈多》的分析中充分显示了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敏锐。一方面,他从这种“等待”中看到了一种现代的英雄主义(类似于加缪的《鼠疫》):“尽管推迟的行为使得人生难以承受,但也可能正是这种行为使得人生处于运动之中”,“如果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那么绝望就是不可能的。”(第60页)“他的文字反常的地方在于,对零零碎碎的意义如学究一般考究,对纯然的空虚也要精雕细琢,狂热地想要言说那不可言说之物。”(第62页)。但另一方面,贝克特的作品又表现了一种“后现代的实证主义”,即就事论事,反对向事物施加某种自以为是的意义。不过,作者从贝克特的这种“次级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中引伸出了他认为合理的东西,即虽然排除了人为的意义,但却仍然认为“事物必须内在地有意义,而不是靠我们钻研出意义”(第64页)。
现在问题在于,这种客观事物的“内在的意义”如何能够被我们所知道、所把握。作者认为,这个问题类似于新教伦理对上帝的态度:“新教徒的自我在随机力量的黑暗世界里胆怯地走动,内心萦绕着一个隐匿的上帝,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得到救赎。”但这又是一次“巨大的解放”,当破除了一切权威的解释之后,一切答案都要靠自己去寻求了。“孤独的新教精神胆怯地在黑暗中摸索,这会是为那些相信人生由自己创造的人感到忧虑的原因吗?既是又否。否,因为创造自己的人生的意义,而不是期待意义被预先给定,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主意。是,因为这应该是一个清醒的警告:人生的意义不是自己能够随心所欲创造的,它并不能免除你的一项责任,即在常识之下证明任何使你的人生有意义的东西的合理性。”“这也不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过程。人类可以自我决断——但只能建立在更深刻的对自然、现实世界的依赖以及人类相互依赖的基础之上。”(第74-75页)这里不太严格地表达了一种“解释学的循环”:对整体的理解有赖于每个个体的创造性,但个人创造又是基于对整体的理解。所谓“不太严格”是指,判断整体的合理性标准不是既定的“常识”,而是不断深入的洞见;人们据以决断的基础也不是对世界的“依赖”,而是对经验的历史回顾、认知和预测。
书的最后一章提出了人生意义的两个着眼点,一个是死亡哲学,一个是实践哲学。首先,作者批评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以“幸福”作为人生的意义基础的传统,认为这是一种自欺欺人。当他说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普遍的特点,即不承认那些令人不快的真相,迫切想要把苦难扫到地毯下面”(第84页)时,我几乎怀疑是否要把这里的“西方”改为“中国”。其实西方文化正视死亡也是一个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巨大传统,柏拉图甚至说“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看来作者并不熟悉这一点。但作者在批评了各种幸福的涵义之后,也提出了一个真正富有洞见的命题:“人生若不包含人们没准备好为之赴死的东西,这种人生就不可能富有成就”(第89页,“没准备好”应为“准备好”之误 )。他认为,“人生即是死亡的预期。我们只有心怀死亡才能活下去。”(第90页)这都很不错。可是他把这种观点与“人生的意义在于思考人生的意义”这种“颇具诱惑力”但却是“同义反复”的命题对立起来,则似乎有些欠考虑。英国学者通常不习惯于思辨,当他们强调实践的时候,他们认为这就是对思辨最好的驳斥,就像第欧根尼用走动来反驳芝诺的运动悖论一样。
所以作者在这里提出的第二个着眼点就是立足于实践,为的是排除思辨。“如果人生有意义,那个意义肯定不是这种沉思性的。人生的意义与其说是一个命题,不如说是一种实践。它不是深奥的真理,而是某种生活形式。”(第92页)所以,“人生的意义便是人生本身”(第93页)。可是,这难道不也是一个“同义反复”?什么是“人生本身”?没有沉思的人生就只剩下吃饭穿衣之类,当然还有“爱”。但作者对“爱”并没有无条件地接受为人生的意义,而是对它进行了一番“沉思性的”解释:“我们称为‘爱’的东西,即我们调和个体实现与社会性动物之本性的方式。因为,爱表示为别人创造发展的空间,同时,别人也为你这么做。每个人的自我实现,成为他人的实现的基础。一旦以这种方式意识到我们的本性,我们便处于最好的状态。”(第95页)不仅如此,这种沉思肯定也应该包含对死的沉思: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人生必有一死,我们才能为自己规划出和为别人创造出发展的“空间”(实际上是“时间”)。所以作者的两个着眼点实际上应该是同一个不可分割的着眼点,即由沉思准备好的实践或者对实践的沉思。它既是“深奥的道理”,同时也是某种经过反思的“生活形式”,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作者最后以爵士乐队的即兴演奏作为自己所推崇的“人生意象”。在爵士乐队中,每个人任意发挥自己的自由个性,但又随时保持着一种接纳性的敏感,与其他队员互相激励和呼应。在这种演奏中所体现的是一种“毫无目的的生活”,在这里,“人生的意义有趣地接近于无意义”(第99页)。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这种没有乐谱的即兴演奏的,这些人必须在长期默契中达成某种共识,必须思考过爱与死这样一些人类共同的问题,他们的各自表达虽然没有明确的主题,但都以各自的个性和特有的方式发表着爱与死的宣言,并从同伴们那里得到应和。人生的意义之所以“接近于无意义”,是因为这个意义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人们在物我两忘中享受着人生的意义。但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决非一日之功,在日常生活中这甚至常常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但正是这一理想不断地激励着人们,要将自己个人的人生意义实现在群体或社会的认同之中。就此而言,我赞同作者的最后一言:“在这样一个危险无处不在的世界中,我们追求共同意义的失败过程既鼓舞斗志,又令人忧虑。”(第99页)
2012年9月9日于喻家山